管理学院 刘宝明
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清华读博时,我所在的社团曾邀请季羡林大师作为学长到清华作过一次报告。如今先生仙逝,其音容笑貌,犹在耳目。悲切之余,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应向大师学什么,而在我脑海中不停闪现的就是“承载”二字。
一部《留德十年》,清新飘逸的文字中却道出了季先生“承载”品格的形成历程。十年寒窗,先生置身于有国不能归、有家不能回的境地,加之大半时间还要忍受战争的摧残,其心理的熬煎可想而知。然而先生“承载”的心理素质,却已在其间历经千锤百炼潜滋暗长。在书中,季先生这样写道,“在那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,人生乐趣仍然是有的。在任何情况下,人生也绝不会只有痛苦,这就是我悟出的禅机。”这便是季先生“承载”品格的真实写照,读后不禁让人感慨良多。
如果说留德十年是季先生“承载”品格的形成期,则后来漫长的国内生涯则是这种品格的表现期。一部《牛棚杂忆》,虽流露出些许酸楚和嗔怪,却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先生“承载”的品格。在开篇中,先生不无诙谐地以一个“比较地狱学”学者自居,讥讽当时牛棚中的罪恶。试想,当年先生在牛棚中九死一生,终日还需与当初迫害的人为伍,此情此景,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愤愤不平乃至心怀报复。而季先生却能以一个老顽童的心态和一个学者的笔触,轻松调侃经历的苦难,先生“承载”的品格让人自叹不如。至于后来在北大校园里,季先生为报到的新生看守行李之类的些许小事,则只能是“承载”品格细小而琐碎的表露。
“承载”意味着理解、宽容、忍让与适应,我们构建和谐社会、建设强盛国家、谋求科学发展,无一不呼唤“承载”之风。而放眼现实,与此相悖的事例比比皆是:从学者们围绕着观点之争或造假之辩的口诛笔伐,到《潜伏》带来的办公室政治观的流行,从时有耳闻的大学生跳楼,到不堪忍受某些快女的演艺而全场喝倒彩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似乎反映出国人的刻薄、急躁而缺乏应有的沉稳与大气,个中原因,缺乏“承载”的品格或是其中之一。
季先生耕耘一生、学富五车、著述等身,供后人汲取的精神遗产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。于我而言,从先生的生平和文字中,领悟到的最直接、最深刻的就是“承载”的品格。中化建设具有全球地位的伟大公司,同样需要“承载”之风。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辛,我们都应该多一些理解,少一些抱怨;多一些踏实,少一些急躁…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中化事业新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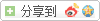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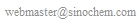 建议(1024*768) IE7.0以上浏览器浏览本站
建议(1024*768) IE7.0以上浏览器浏览本站




